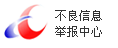|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发展道路虽然相当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息过。究其原因,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我们回首历史,应该能够发现,孔夫子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而儒学的发展,也依然一代又一代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无疑,糟粕是有的,但我们无法舍弃的,是那里的精华。让我们走进儒家思想,考虑一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中国未来的影响。
先看,何谓“儒”?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便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孔子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对礼乐文化进行反思,把有生命力的原则发掘出来,建构了儒家学说体系,是文化转轨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再看,何谓本文所要探讨的“儒家思想”?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向善的,是好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尽管后来出现了荀子的“性恶论”与之抗衡,但其终究没有被中国的大众所接受,只是停留在一种学术思想的层面,这里可以抛开不谈。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国的主要思路就是教育,这也是在当时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的。儒家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那么治理社会就应该从教育入手,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那么社会自然就会安宁了。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 对于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礼”,因为是儒家的“克己复礼”使中国成为了现在的礼仪之邦;有的认为是“仁”,因为这是儒家道德规范之本。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即“仁”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中国人对“人”的态度之上,将在下文详细叙述,这里不累赘。
儒家不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便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智慧并取得了成功。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 儒者毕生追求的只是“君子”——那种集“仁”与“信”、“智”与“直”于一身,内在涵养与外在处世都和谐,永远不失”中庸”的君子,那种清醒自制、静观自身、含而不露、压抑激情的圣人。儒家注重自身修养约束,亦注重社会秩序的制约。儒家思想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当儒教自身特性与封建社会本质相融合之后,便出现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的现实最终为君主所重,奉为经典,扶为正教,大力推广,以其社会伦理观自上而下全面推及,使之渗入社会每个角落。从此儒家便真正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定了其高于百家之上的至尊地位,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之文化主流。这种突出,决非主观意识决定,而是历史的必然决定。
这要回归到“仁”的问题。
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 仁要求人们以人为人,相亲相爱,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醒,对人类的本质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仁者爱人的精义是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的价值,把别人也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人来看待。儒家虽未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对世间事务的重视却远远重于对鬼神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展现高于对灵魂有无的探究,这种人本观念使其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而中国古代虽然也讲神设教,但宗教思想一直未能像西方那样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支柱和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的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任何人一生下来首先遇到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关系,处于亲人的爱抚之中,并逐渐萌生对亲人深深的依恋、情爱。因此,家庭中的亲爱,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后来儒家也以亲亲敬长解释仁的基本含义。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末。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爱心,爱人就是爱亲之心的外展与扩充,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直至今日,我们尚可闻见“百善孝为先”之类在历史中已流传两千余年的教训;“不孝子孙”成为了最为人们所不齿的一类人。可见儒家的仁爱之根本已经深深的进入了中国人的骨髓,难以磨灭了。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它必须通过显示的行为表现出来。因而,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去爱人,就成为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儒家提出的行为模式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南宋朱熹解释说:“尽已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卷二)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它们是以仁推己及人的两个方面。 “忠”是积极一方。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作为“为仁之方”的行为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积极使别人也同样得到。“恕”是消极一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
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离开了道德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人,不仅不能利人,适足以害人。因此,儒家提倡仁者爱人,特别强调爱人以道,爱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已然后能推人。那么,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体措施就是“克己复礼”。具体的讲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礼(社会道德)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行即所有行为都符合于礼,克制自身与道德相违背的一切私念和欲念,从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并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几乎都遵循着它当年的步履。儒家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如今的三岁小儿也都能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君子”之方,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为人最高境界;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从而这种“礼”与“义”的准则始终牵制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在以上所有的基础之上,中国人代代相连,从而建立起了复杂而又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与中国政治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实现民主转型。他们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或许对于儒家思想的本身已经有了歪曲与误解。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中国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邻国——那些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比方说日本,它从明治维新便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二战后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九十年代又开始从“一党独大”体制向“政党轮替”体制演变。近十几年来,韩国等更接近儒教文明中心的地区也相继实现了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新加坡则正在从足够自由而缺乏民主的政体向更加民主的政体过渡。为何我们的邻国纷纷改革着自己的制度,反而是中国这个儒家文明的发源地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而蹒跚难以前行呢?
或许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走过的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哪里,则是有争议的。以往,人们更看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几乎成了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近来则有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张灏更明确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把“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提前到世纪之交,或许有助于正确理解儒家思想与中国民主的关系。
民主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乡土主义、宪法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多种价值的复合体。这些思想的大部分生长点都可以从儒学传统中发掘出来。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 “西学”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掘自传统的“中学”。康有为从公羊学平滑过渡到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的制度雏形。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儒学传统并没有对国人接受民主思想构成障碍,而是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 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陈独秀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呼吁,他断言:“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按照这种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人就没有资格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碍,不是从政治实践上着手逐步的解决,而是在伦理思想上寻求根本的解决,这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思想误区。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便有了一种“新的崇拜”。北大教授陈百年在1923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曲折,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过于保守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过于趋新以及世界时髦思潮造成的负面作用。 在政治领域,西方文明的长处是“善政”、“良制”,儒教文明的长处是“善治”、“良吏”。我们推动民主化进程,要从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传统中吸取养分。儒家思想不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之一。真正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思想因素,并不是“三纲六纪”之类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各阶层人士的一系列现实考量。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应该学着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与均衡中把握住民主转型的契机,把“善政”与“善治”更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 儒家思想在21世纪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他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而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同时我们也在用自己思维的进步,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 现在有人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然而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却遭遇到了尴尬和难堪。因为人们没有注意到,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通过研究一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能办得到的。如此固然可以发掘、拓展出一种新的意义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损害了既往时代活跃的生命运动和富裕的精神生命。 由于这样的“改革”遭到失败,人们便渐渐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有一种“儒家思想过时了”的想法在蔓延。然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义理。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应当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自然,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处于不断的改造与更新当中,否则便容易僵化。儒家文化是古代的东西,与今天的社会确实会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学问也需要调整。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要继承,但是,同时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继承,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知识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说 “儒家思想过时了”是不正确的。只要能够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不抱残守旧,不照搬照抄,那么,这一悠久的文明就能在现实生活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不能长期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循规蹈矩,而应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模式。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才能完全展现其超时代的价值。 |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网站地图
网站地图 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添加收藏
添加收藏 设为主页
设为主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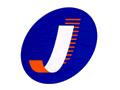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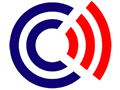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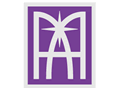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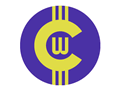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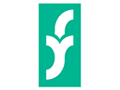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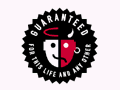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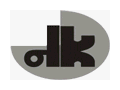

 www.kyyzw.com/main.asp 本网站是由:中国北方周易学会主办,是国内唯一的专业开运印章网,本单位投入巨资从福建寿山,浙江青田,蒙古巴林,黑龙江等地直接定采瑰宝田黄玉,寿山玉,青田玉,巴林美玉等质地鲜艳通灵,古意蛊然,凝腻质润,色彩鲜艳多斑纹,质明净,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的价值的美玉开运印章料,出售价位低于市场的几倍,为客户刻制吉祥开运印章,并负责请大德高僧法师开光,欢迎有识之士订购选用。瑰宝田黄玉,寿山玉,青田玉等不同与其它珠宝艺品,随着日益开发开采的数量的减少,做开运印章还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即为自己开运旺运气,又能收藏玉器珍宝而投资获利。最主要的是用这种符合本人喜用神的天然玉质,雕刻上本人的名字作为开运印章,能胜过一个专家起的吉祥的新名字,当然如宝宝用专家起的吉祥的名字在配上开运印章,那更是锦上添花,吉祥万千。 学生学业差使用吉祥开运印章补助,可使学业转为优良,财运差使用吉祥开运印章补助,可使财运倍增,求官者用马上封候吉祥开运印章,可使官运亨通,吉祥开运印章还利于工作,事业,身体健康,风水不利,炒股票,抓奖券等。请加QQ:764765592,也可搜:中国玄术子开运印章网,网址:www.xszxm.cn/bdzlw/index.asp 咨询电话:022--22167503
www.kyyzw.com/main.asp 本网站是由:中国北方周易学会主办,是国内唯一的专业开运印章网,本单位投入巨资从福建寿山,浙江青田,蒙古巴林,黑龙江等地直接定采瑰宝田黄玉,寿山玉,青田玉,巴林美玉等质地鲜艳通灵,古意蛊然,凝腻质润,色彩鲜艳多斑纹,质明净,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的价值的美玉开运印章料,出售价位低于市场的几倍,为客户刻制吉祥开运印章,并负责请大德高僧法师开光,欢迎有识之士订购选用。瑰宝田黄玉,寿山玉,青田玉等不同与其它珠宝艺品,随着日益开发开采的数量的减少,做开运印章还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即为自己开运旺运气,又能收藏玉器珍宝而投资获利。最主要的是用这种符合本人喜用神的天然玉质,雕刻上本人的名字作为开运印章,能胜过一个专家起的吉祥的新名字,当然如宝宝用专家起的吉祥的名字在配上开运印章,那更是锦上添花,吉祥万千。 学生学业差使用吉祥开运印章补助,可使学业转为优良,财运差使用吉祥开运印章补助,可使财运倍增,求官者用马上封候吉祥开运印章,可使官运亨通,吉祥开运印章还利于工作,事业,身体健康,风水不利,炒股票,抓奖券等。请加QQ:764765592,也可搜:中国玄术子开运印章网,网址:www.xszxm.cn/bdzlw/index.asp 咨询电话:022--22167503










 http://www.xszqm.cn/substation.asp?link_id=202
http://www.xszqm.cn/substation.asp?link_id=202